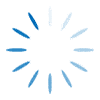皇帝自当政以来, 一直致力于肃清吏治, 云阳伯此举, 无意识撞上了枪口。皇帝震怒,要求刑部彻查此案,且由祁王督办。
禹王原本还胸有成竹, 刑部一大半都是他的人, 只要他稍作提点, 这件事根本翻不起浪花来,谁知陛下竟然让祈王来督办此事。
要说这些时日, 皇帝经常宣祁王入宫,两人一待就是大半日。朝中早就有人议论,陛下属意立祈王为太子。
如今陛下由此举动,是在放着他,还是再为祈王造势?
禹王看不明白,只能尽力从中调和,好不让自己这件事连累到自己。
好在祈王也不是草包,很快便找到了云阳伯受贿卖官的证据, 顺带着还牵连出了当年的粮草失踪案。
当年之事,沈家军可谓是损失惨重, 沈檐在朝堂上声泪俱下跪求陛下彻查,还死去的冤魂一个公道。
所谓纸包不住火,当年禹王年轻气盛, 身边又无牵制,办事自然是诸多漏洞,根本就经不住查。
云阳伯被下了大狱,紧接着,姚志远,徐闯,越来越多的与当年之事有牵连的人被查了出来。
面对种种证据,禹王只说自己是被蒙蔽其中,并不知情,云阳伯也亲口承认,一切都是他贪图钱财,与旁人无关。
明眼人都知道这事指定跟禹王脱不开关系,可奈何没有证据,皇帝也只是训斥了禹王几句,罚他禁了足。
最终,云阳伯被削去爵位,判秋后问斩,家产充公,家中男子全都发配戍守边疆,女子皆发卖为奴。
云阳伯府被抄家那一日,傅云修心情颇好的要和阿满去城外踏青。
“踏青,现在吗?”阿满很是疑惑。如今都快要入夏了,踏什么青。
“索性今日天气好,出去走走也无妨。”傅云修推着阿满出门,甚至一早就租好了马车在门外等着。
马蹄声“哒哒哒”的落在青石板上,阿满看着车里气定神闲喝茶的某人,一脑袋的疑问。直到听到外头的哭闹声。
“公子,前面有官兵堵了路,暂时过不去了。”车夫说。
“既然过不去,等等也无妨。”傅云修说。
外头声音吵吵嚷嚷,阿满着实好奇的很,便掀开车帘去看。
人头攒动间,阿满远远便看见那只是回忆起来,都让人骨头生寒的云阳伯府。
昔日气派的府邸,如今已乱作一团。门头的匾额被打落,四分五裂地散落一地。门口,一群带刀的官兵横眉冷对。男人的哀嚎声,女人的哭喊声此起彼伏。
阿满几乎是一眼就在人群中锁定了那个曾经不听她辩驳分毫,就下令让下人折磨她的姚氏。如今她风光不在,身上的锦衣华服已经变成了粗布麻衣,发髻胡乱的歪斜着,甚至还有几缕头发散落鬓间,似乎是被人拔去头上的发饰所致。
她跌坐在一众女子中间,怀中抱着的小儿啼哭不止她也顾不上,只一味说:“我不是,我不是,我不是姚夫人,你们弄错人了。”
“放了我,放了我。”说着,她抱着孩子想要冲出包围圈去,却被守卫的士兵狠狠的摔在了地上,啐了一口,“疯婆子。”
很快,一箱箱的金银财宝被抬出来,原本已经哭累了的众人,瞬间又开始哭天抹泪。
现在他们终于信了,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已经不在,往后等着他们的,唯有无尽的贫穷与苦楚。
抄家的官兵终于走了,云阳府众人也被收入大狱,等待发配和变卖。
围观的群众看了一场好戏,都有些意犹未尽,相信接下来的半月,邕州的谈资都离不开云阳伯府。
道路终于通畅,马蹄声再次“哒哒”响起。
阿满收回了视线,坐在马车里,良久都不曾说过一句话。
傅云修小心地看了她一眼,没有想象中的喜悦,亦没有对他们的怜悯与同情。一时间,浮傅云修竟吃不准阿满的心思。
“阿满。”傅云修低低地唤了一声,可话到嘴边,他却不知道该如何询问出口。
你生气了吗?
或者问,你解气了吗?
似乎怎么问都不对。
两人相对无言,直到马车出了城,车夫说他尿急要去方便后,阿满这才开了口。
“公子,云阳伯府有今日,是不是你的手笔?”阿满不是傻子,此前傅云修约她出来踏青她就觉得不对劲,如今算是为她答疑解惑了。
踏青是假,只要是想让她看着一场好戏吧。
“是。”面对阿满的询问,傅云修一时有些无言。
她知道阿满心善,方才云阳伯府众人被带走时的场景,他看了都有些不忍,又何况阿满。
这其中,总会牵连到无辜之人。
“是,阿满,所以……”傅云修语气晦涩,甚至有些不敢看阿满的眼睛,“这才是真正的我阿满,如你所见,我并不是个好人。”
那些人或许无辜,但他却并不会同情,更不会后悔。
这世上无辜枉死之人有多少,那些曾经被云阳伯府害死的百姓就不无辜吗,那些因为缺衣少食,冻饿而死的沈家军就不无辜吗?
他们既然享受了云阳伯府的权势与荣耀,那罪责与惩罚,他们也要一并受着。
这一路来,傅云修心中忐忑不安,如今,他跟是紧握双手,等着阿满给他的判罚。然而想象中的冰冷的言语并未到来,而是阿满那双温暖的小手,环上了他的腰。
阿满抱紧了他,脑袋贴在傅云修胸口,这才缓缓出声, “公子,其实,我也不是好人。”
做好人太难了。
阿婆与人为善,得到的是宠妾灭妻,不得不带着女儿远走他乡。
母亲与人为善,等待她的是主母的磋磨,夫君的抛弃。
她不想步了她们的后尘。
云阳伯府一事,她不与姚氏计较,并非是她大度,而是因为她蜉蝣之力,完全没法和姚氏抗衡。否则,姚氏打她十鞭,她必定百鞭千鞭的还回去。
如今公子为她报了仇,她自然是心中痛快。
至于云阳伯府的其他人,让他们到抄家流放这步田地的并非是她阿满,而是云阳伯。她没什么好愧疚的。
方才在车上她一直不说话,一方面是因为心中的震惊,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有那车夫在。
公子曾说过,那云阳伯与禹王关系颇深,她虽不知道公子究竟做了什么,但到底还是怕的。
所以直到车夫离开,她才敢开口。
阿满知道,公子这么做,只是因为她在云阳伯府受了虐待。
阿满抱紧了傅云修,埋在他胸口的脑袋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,心里一阵害怕,“一定很辛苦吧!”
他身子刚好没多久,都没怎么好好休养,就为了帮她报仇四处奔波。着其中的苦楚,可想而知。
傅云修并没有回她的话,只是轻柔的在她额上落下一个吻,“阿满,从今往后,我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辱了你。”
云阳伯府一事结束后,阿满的日子过得越发的恣意。
每日雷打不动的出摊,空余的时间,便在家里,跟着傅云修一块儿写写字,作作画。
两人腻腻歪歪,一旁的馒头直呼没眼看,却又咧着嘴角笑个不停。
期间,傅夫人来过几次。借口说是看望,但话里话外,都是在警告傅云修,不要肖想自己不该肖想的东西。
只因这些时日,不少族老觉得侯府一直爵位空悬,而傅云修作为嫡长子,理应继承爵位。
这样的话,傅云修耳朵都听出茧子了,便随着她念,丝毫不放在心上。
一场大风过后,天气阴沉,乌云密布,一副山雨欲来之势。
阿满将外头晒着的花瓣收进屋里,看着暮色沉沉,心中一阵发愁。
“看起来是要变天了啊!”
这一下雨,不知道又要有多少花朵被打落。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!
“别担心,你夫君我现在一幅画价值千金,到时候补给你就是了。”傅云修走过来,揽着她的肩头将她带进屋里。
“什么夫君,不知羞。”阿满被他说得脸热,忍不住伸手去捏他腰间的软肉,却被傅云修轻笑着躲过。
连连求饶,“好阿满,是我胡言,是我胡言。”
梧桐苑这边满是欢声笑语,但侯府那边,却是愁云密布。
因为——京城真的变天了。
禹王他,反了。
七日前皇帝祭天,选了祁王陪同进香,祭天仪式上突然出现了刺客,皇帝被刺中胸口,性命垂危。
刺客落网后,承认是受祁王指使。然祁王眼下正陪着皇帝,还下令严守皇城,不许任何人探视皇帝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