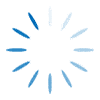看着明明跟我同届的君怡对于未来縝密的规划,我开始对未来感到焦虑,那些不切实际的粉红泡泡,也一点一点消散了,与其胡思乱想,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眼前该完成的事情上。
至少,这样比较不会让人心烦意乱。
这段时间,我和林家同的关係,就像最普通不过的朋友,甚至曖昧也搭不上边。
没事的时候,不会特别联络,没有早安晚安,也没有谁在忙什么的日常报备,这样也对,毕竟我跟他从不在同个生活圈。
甚至知道他的动态,也是从宇皓学长口中得知。
那天下午,我在饮料店上班。
正值最忙的时段,街道上此起彼落的汽机车喇叭声,和店内流动的爵士乐交错成一片嘈杂。
我一边接着电话点单,一边听着印贴机不间断地吐出单子,长长一排垂到地上。
我和曼琳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间,双手忙着封膜、摇杯,把眼前这笔大单一杯一杯地消化掉。
我低着头摇着饮料,却在抬眼的瞬间,看见了熟悉的身影是林家同。
他和一群朋友一起走进来,笑得很开心,像是聊到什么有趣的事。
「嗨,诗婷!」他主动向我打招呼,也是他第一次喊我的名字。
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,浅笑回应,很快又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。
直到他朋友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「欸,你怎么到处都认识妹子啊?」
「对啊,哪里都有你认识的人。」
「我们学校的喔?哪个系?」
「你连摇茶的也要亏人家是不是?」
那些话带着玩笑的语气,却让人听了很不舒服。
我低着头装作没听见,手却不自觉地握紧了杯子。
家同没有接话,只是安静了一下。
等我把饮料递过去时,他靠近了一点,压低声音对我说:「抱歉,我不知道他们讲话这么欠揍,早知道就不要带他们来了。」
我停顿了一下,抬头看他。
他眼神里带着一点歉意,还有一点小心翼翼,深怕我生气的样子。
我点了点头,知道说错话的人不是他,连忙补上:「没事啦。」
话是这样说,但我的表情大概出卖了我自己。
他没有马上离开,又问了一句:「你还好吗?感觉有点不开心。」
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情绪面对他,只能臭着脸回答:「没有啦,最近压力比较大而已。」
他似乎不太相信,站在原地想再追问什么。
但我不想在眾人面前谈这些,他也察觉到了,只好作罢。
后来,他们离开没多久,我的手机震了一下。
我盯着萤幕看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打字。
「最近有点焦虑未来,觉得自己每天都一样,好像很没用,然后听到你朋友又叫我摇茶的,觉得自己更没用了。」
讯息送出去的那一刻,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害怕他的回应。
「你明明要打工、又要上课,早八也从来没迟到。」
「我觉得你很乖,也很尽责,不应该把自己说得那么差劲。」
「真的,你已经很棒了。」
「是那种,已经超棒的那种。」
那些字一句一句跳出来,我的胸口暖和了起来。
接着,他也开始说起自己的烦恼。
他说他其实也很焦虑毕业,很想赶快当完兵,再去找工作。兵役卡在那里,什么计画都很难开始。
他甚至有点自嘲地说,自己念这个科系,未来大概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,薪水一定很低。
「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好像完蛋了。」他打完,又补了一个苦笑的表情符号。
那一天,我们没有聊爱情。
只是在讯息里,笨拙地安慰彼此。
「日復一日地活着,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事。」
「不要再这样说自己了。」
忽然间我觉得这一切的努力可以被别人理解,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也许是因为家同给出的那份同理心,我们之后更常聊天了。
我会不自觉地想跟他分享日常,比如今天早八差点迟到、打工时遇到的怪客人、午餐吃了什么。
那些原本只会留在心里的小事,开始有了一个可以传送的对象。
即使他的回应不算即时,有时候也不会秒读秒回,可我的情绪却总能被他稳稳地接住。
那样就够了。我其实,很快乐。
某天。上课上到一半,我的手机震了一下。
萤幕亮起,是妈妈传来的讯息。
那一瞬间,我脑袋一片空白,理智线像是被人硬生生扯断。
我连请假的话都来不及跟老师说清楚,只抓着手机站起来,快步走出教室。
走廊很长,我一路往最里面走去,手指颤抖地拨了电话。
电话那头,妈妈的声音显得慌张。
她说,这几天阿妹几乎没有吃东西,带去给兽医看,医生只是摇头,说牠年纪大了,就算打点滴,也只是延长时间而已。
「所以我跟你爸爸就把牠带回家了,」妈妈停顿了一下,「我们不敢跟你说,怕你上课跑回来。」
她继续说,刚刚看见阿妹一直睡,怎么叫都叫不醒。眼睛微微张着,呼吸明显变得很弱。
我握着手机,整个人靠在墙上,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,完全止不住。
我知道阿妹已经很努力了。十五年,牠陪着我长大,我也陪着牠变老,牠明明走路已经很慢很慢了,又在我每次回家时,总是热情的迎接我,用牠小小的身子想扑倒我,用牠明明能见度很差的视力,像在跟我说,我知道是你回家囉,我认出你囉。
但现在,身为姊姊,我一句话都挤不出来。
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,好想在你身边,摸摸你。好想陪你走完这一段。
对不起,姐姐今天没有在你身边。
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几秒。
然后,妈妈哽咽着说:「阿妹走了。」
那一刻,我的世界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。
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得很伤心,我却只觉得胸口空了一大块,什么声音都进不来。
我轻声说:「我下午请假,回去看牠。」
掛掉电话后,我站在走廊深处,眼泪怎么擦都擦不乾。
就在这时,有人轻轻碰了我一下肩膀。
我慌忙抹掉脸上的眼泪,转过头。
家同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,手上却已经帮我把包包拿了出来,背在自己肩上。
他没有问,也没有说话。只是用一个很安静、很心疼的眼神看着我。
那个眼神,像是在说:我知道了,你不用解释。
下一秒,我的眼泪彻底溃堤。
我接过包包,小声说了一句:「谢谢。」
他没有追上来,也没在那一刻多问。但那一秒,我心里很清楚,有些人,只要站在那里,就已经给了足够的力量。
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额头轻轻贴着冰凉的玻璃,感觉自己好像离阿妹更近了一点。
窗外的景色一格一格地往后退,田野、街道、模糊成一条拉长的线。而我只是呆呆地看着,脑袋却什么也装不下。
有些存在,一转眼就被时间带走了。
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后,我还是拿起了手机,传讯息给家同,我想谢谢他的贴心。
「刚刚来不及跟你解释就跑走,是因为阿妹走了,我有点太激动了。」
讯息送出后,我盯着萤幕看了很久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,又打了一段。
「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没回去看阿妹了。」
「我根本不是什么好姐姐,连牠走的时候都没在牠旁边。」
「阿妹只是先去当天使了。」
「牠一定很幸运能认识你,所以你不要太内疚。」
他的话总是这样,没有过多的形容,却总是说在我心上头。
看着那几行字,我的眼眶又热了一下。
然后,一个不该出现的念头,悄悄浮了上来。
我盯着对话框,手指停在键盘上,犹豫了很久。
理智告诉我不该问,可情绪却推着我往前一步。
最后,我还是衝动地打了那句话。
「你会觉得,遇到我也很幸运吗……」
讯息送出的瞬间,我的心跳快得不像话,即使我知道他的回答,对于我来说不是大好就是大坏,但我想知道他到底只是把我当朋友还是我们之间有可能。
「可以认识这么好的人,当然幸运。」还比了一个讚。
我盯着那个讚的表情,看了很久。
那句话没有错,也没有拒绝。可它没有重量,没有方向,更没有我期待的那个答案。
这宛如是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,谁也没说破,却都隐约知道,界线就停在那里。
Tom听完后,沉默了一下,才说:「其实这样听起来,他对你还蛮贴心的。」
他停顿了一秒,又说一句:「那他……没有想过要往下一步吗?」
「他一直都是这样,不上不下的回应。」我轻声说,「没有拒绝,也没有前进。」
我抿了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,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。
「直到他因为一些事情,需要我帮忙,我们才越走越近。」
我请了两天的班,幸亏饮料店店长也很体谅,让我可以回家处理阿妹的丧事。有时候都会想,毛小孩对于人类是怎样的一个存在?难道就像大家说的,你是牠的一辈子,而牠只是你人生的一个片段,但明明我现在就可以推翻这件事情,我只想要我的「阿妹」,对于我来说牠的存在,只会是唯一,世界上就算有长的再像的贵宾狗,牠也不会是「阿妹」。
宇皓学长看起来从家同那边知道了这个讯息,也来关心我的状况。
「我可以理解你狗狗离去的痛。」
「你要相信牠会在汪星球找到好朋友,然后变成最亮的一颗星,看着你。」
宇皓学长的话也给了我很多力量,他是校园出了名的爱狗人士,我相信他也经歷了许多与狗的别离才能这么坦然的面对生死了。
他还提醒我,怕我无聊,说校狗一零一可以有空去摸摸牠,校狗一零一是一隻白黑斑块的土狗,长得很像盗版的大麦町犬,牠很活泼,可以给人类满满的情绪价值。
处理完阿妹的告别式后,我回到学校。生活像是被人按下重啟键,所有事情照常运转,只有我慢了半拍。
后来有一次,家同传讯息给我,说知道我读护理,有个问题想諮询我。
我原本以为,是什么课业或报告的事。没想到,他传来的,是一张模糊的照片。
「我脚踝的伤口好像有点怪怪的。」
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,不免困惑,这是哪里的伤口。
他平时脚上都穿戴助行靴完全不会想到他的车祸伤口还未痊癒。
他说,回诊时医生告诉他,伤口恢復得不好,如果没有好好照顾,可能会引发蜂窝性组织炎,再严重一点,甚至有截肢的风险。
「我有点害怕。」他打了这样一句话。
我回他:「先不要想那么多,好好照顾比较重要。」
然后,我请他把伤口拍清楚一点给我看。
不看还好,一看,我整个人坐直了。
那个伤口红肿得不像话,皮肤紧绷,顏色深得不自然。
「肿成这样,跟麵龟一样,你都不会痛喔?」我忍不住问。
「会痛就代表异常啊。」我回得很直接。
他隔了一下才说:「我想说……会不会只是每个人耐痛度不同而已。」
我深吸了一口气,开始问他平常怎么换药。
「就生理食盐水,然后优碘,再包纱布。」
他打得很简短,像是在背一个早就熟记的流程。
但我几乎可以确定,问题不在药物,而在方式。
我盯着手机萤幕,犹豫了几秒,还是打出那句话。
「不然……我帮你换药看看?」
说出口的瞬间,突然觉得自己很唐突,我后悔了。
结果,他回得比我想像中快。
那一刻,我的心跳,毫无预警地快了一拍。
我照着导航骑车过去,才发现这里离学校其实有段距离,不太像本校学生会选择的地点。
这一带聚集了几间大专院校,出租给学生的套房很多。格局几乎都差不多就一张单人加大床、一张书桌、一个衣柜,再加上一间小小的浴室。
当时选择住宿舍时,也是因为看到外面的出租套房价钱不便宜,空间也很窄小,不如住宿舍,方便又省钱。
不过说真的,我从来没有去过异性的宿舍。
一路上,我心里有点乱。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紧张。
我什么都没带,他说换药的材料他那边都有。
我把摩托车停在楼下,传讯息给他:「我到了。」
他拆掉了脚上的护具,一拐一拐地走下楼。
那一瞬间,我突然明白了,他之前走得那么自然,其实都是撑出来的。
这个人,真的很缺人照顾,逞什么强。
他住在三楼,楼层不高。
「你慢慢走就好,不急。」我走在他后面忍不住提醒。
他的房间,比我想像中乾净,乾净得不像是男生的房间,连电脑桌都整理得很整齐,东西各自归位,没有多馀的杂物。
我有点讶异,脱口而出:「你是不是偷偷整理过?」
他挑了下眉,「不要说得好像男生都很骯脏好吗。」
「没有贬义啦,」我赶紧解释,「就是……有点意外而已。」
房间里有淡淡的洗衣精味道,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一样。
空间不大,和我想像中的学生套房没有差别。
难怪他说,等以后要住在一间前面有大草地的房子,才能养杜宾。
我站在窗边往外看,心里却突然冒出一个不该有的念头,如果那个画面里,也有我就好了。
我们一起养杜宾,陪牠玩你丢我捡的游戏。
然后我跟家同可以在草皮铺着一块布,我们躺在草皮上,看着天空。
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,赶紧回过神。
这时,他已经把换药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我面前。
拆好的纱布、打开的生理食盐水、优碘,还有一包已经拆封的棉棒。
「这个生理食盐水,开多久了?」这是那种二十毫升、方便携带的轻巧瓶。
「应该……这礼拜开的吧。」他想了想。
我指了指旁边的棉棒,「那这个呢?」
「上次换药没用完,就留到现在。」
我脑袋里瞬间跳出四个字—无菌原则。
没有多说什么,我直接把那些我看不下去的卫材全丢进垃圾桶。
「欸,不能用吗?」他有点惊讶。
「开这么久早就不乾净了,」我语气很直接,「无菌都不无菌了。」
他嘀咕了一句:「这样不是很浪费吗?」
我转头看他,没好气地说:「你要钱,还是要腿?」
他愣了一下,立刻改口:「我要腿。」
那瞬间,我差点笑出来。
他的脚被我抬起,腾空放在椅子上。
房间本来就不大,我只能坐在床缘的位置。
他乾脆拉了张椅子,坐在我同侧,距离近得只剩下一隻手臂。
我蹲不下来,只能弯着身子替他处理伤口。
生理食盐水倒下去的瞬间,我还是先提醒了一句:「会痛一下,不要动喔。」
下一秒,他整个人明显僵了一下,眉头皱得很深,甚至下意识地咬住了自己的衣角,没有出声。
「你这个伤口之前一定没有洗乾净,」我一边动作,一边说,像是在分散他的注意力,「不这样处理,是不会好的。」
他只是低低地应了一声,额头渗出细汗。
「这些用不完的就丢掉,」我语气变得很专业,「不然很容易长细菌。」
他点头,表情却已经狰狞到不像话。
我专心地替他清洁、消毒、重新换上乾净的纱布,动作小心又缓慢,深怕一个不注意又让他多痛一下。
「好了,」我最后拍了拍他的脚踝,「OK,大功告成。」
我抬起头的瞬间,才突然意识到,我们靠得好像有点太近了。
近到我能清楚听见他的呼吸声,也近到,我几乎分不清那急促的节奏,到底是他的,还是我的。
空气像是被什么东西填满,变得很安静。
我下意识地往后挪了一点,拉开距离,几乎是立刻开口说话,想把那份突如其来的尷尬填补起来。
「其实很简单吧,」我故作轻松地说,「你之后就照这样换就对了。」
话一说出口,我才发现,自己连声音,都比平常高了一点。
他也很快察觉到了那份微妙的气氛。
像是忽然意识到什么,他清了清喉咙,语气刻意变得轻松。
「不愧是专业的,」他笑了一下,「谢谢。」
我顺着他的话点了点头,把用过的棉棒和包装纸收进垃圾袋,动作刻意俐落,好像只要忙起来,就能假装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「之后记得每天换,」我低头说,「不要再偷懒了。」
「好啦好啦,」他应得很快,「我会乖乖照做。」
我们之间重新变回那种看似安全的距离。
离开他家之后,我其实以为,回到宿舍没多久,他就会再传讯息给我。
也许是约下一次换药,也许只是很平常地问一句「回到家了吗」。
接下来的几天,他开始刻意和我保持距离。
回讯息的速度变慢了,语气也变得简短。
我不知道他是在欲情故纵,还是单纯不想再往前一步。
但这样被他用「躲避」的方式对待,也不是第一天了。
我一边说服自己不要多想,一边又忍不住想。
如果他不过来,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努力,再靠近他一点点?
期中后,君怡成功的应徵上了诊所柜檯。
工作一忙起来,她几乎没有时间再去看篮球赛,毕竟我们这种日校学生,只能趁空堂打工还有当晚间工读。
有一晚她突然问我,明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看系篮。
我低头看了一眼赛程是休间运动管理系对资管系。
几乎没有半秒犹豫,我就答应了。
「上次那个很厉害的65号没有打了,」君怡随口说。
我没有告诉她,我其实认识65号。更没有说,我现在,甚至还有点喜欢他。
当天去体育馆时,球场上少了他,气氛明显不一样,像是少了某种灵魂。
对方实力坚强,分数一路被拉开,球怎么投怎么进,几乎没有给资管系喘息的空间。
今天资管系的运气显然不好。
比赛结束时,我和君怡默默走出体育馆,就在出口附近,我认出了一个熟悉的背影。
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偷偷跑来看比赛的,也不知道他看了多久。
他手上和脚上的护具都已经拆掉了,但走路的速度明显比平常慢。
我不知道他都来了怎么没上看台看,还是他在担心什么?
我跟君怡慢慢往宿舍移动,就在这时,一阵歌声从不远处传来。
我们被舞台上清亮的嗓音吸引,不自觉地往声音的方向靠近。
原来是吉他社的成果发表会。
我们没有并肩,只是在人群里,朝同一个方向移动。
舞台上的人是我一直觉得很酷的那个女生。
原来,她不只穿搭风格特别,连歌声也这么好听。
表演结束后,台下观眾纷纷欢呼,她对着麦克风自我介绍。
「大家好,我是伍伊琳,绰号510。」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。
甚至还去查了她的名字,发现她有粉丝专页。
「她唱歌很好听耶!」君怡也称讚。
我站在远处,偷偷看着家同。
他的目光没有移开,那是一种毫不掩饰的专注。
我忽然很清楚地意识到,他看向舞台的眼神,和他看向我时,是不一样的。
我点开了伍伊琳的粉丝专页。
她常常分享生活日志,也勇于放上自己的自拍照,画面里的她,看起来表里如一。
穿搭有个性,神情却很自然,不刻意讨好谁,率性、洒脱,形容她很贴切
我一张一张地滑着,没有快转。
越看,越清楚地意识到,她不是经营出来的那种女生,她只是很自在地做自己。
我开始注意她穿的衣服、搭配的方式,偷偷把一些她会穿的风格存进购物车。
我不知道这招对家同来说管不管用?但我想到他那时看着伍伊琳唱歌的眼神,我竟然显得吃味。
后来,我买了几件平常不太敢尝试的衣服,像剪裁贴身、透肤材质。
穿上后就连镜子里的自己,看起来有点陌生。
想讨好家同……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。
只是很单纯地想,如果我看起来不一样一点,他是不是就会多注意我一点?
可在试穿的时候,我却突然停了下来。
我为什么要打扮得像伍伊琳?
明明我知道,那不是我。我不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自在的人,也不是一站上舞台就能发光的女生。
可如果这样做,真的能让林家同多看我一眼,那是不是……也没有那么糟?我至少被看见了。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,我自己都吓了一下。
我不知道这样的我,算不算卑微。我只知道,我现在真的很想被他注意。
即使,是用一个不像自己的方式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