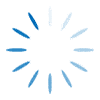宇皓学长的情报显然派不上用场,但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我只能像个徵信社,从与家同过往的对话碎片里拼凑线索。
他说过,他们家是那一带小有名气的杂货店,家门口转个弯就是一间香火繚绕的妈祖庙。
我盘腿坐在床,打开Google地图,将家同老家那个乡镇的所有杂货店一个个点开。指尖在萤幕上滑动,街景图一张张掠过,终于,在一个偏僻却温馨的巷口,我看见了一间完全符合描述的老旧招牌,转角处,庙宇的飞簷隐约可见。
我想,林家同肯定没料到我会真的找上门吧。我就是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「恋爱脑」,区区三十公里算什么?只要能在那条巷口看见他惊讶又欣喜的神情,再远的距离都不怕。
我把这个「週末大计画」分享给君怡,她听完后直呼我太热血。随后,我们聊起了实习的苦水。她在台北实习压力大到让她在电话那头哽咽,而我除了安慰,只能陪着她一起叹气。我们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,在深夜里互相打气,希望彼此都能撑过这段被榨乾的日子,然后擦乾眼泪,继续在前行。
护理系的规矩多得像军队。伍伊琳听从老师的命令,下班后就去买了卸甲液和卸睫毛的药水。
我在一旁看着她处理。卸除药剂的味道很刺鼻,燻得她那双原本锐利的眼睛红通通的,看起来竟有些楚楚可怜。
「你不觉得我们很像在当兵吗?」我蹲在她身边,有些担忧地看着她红肿的眼眶。
「某个程度来说,确实挺像的。」她闭着眼,语气依然酷酷的。
「做指甲不行,贴睫毛也不可以,还有什么可以的?」
「其实我还好啦。」伍伊琳自嘲地笑了笑,「我以前待的那间学校更夸张,规定要吃素,不成文的教条一堆。像我这种打扮,在那边根本是异类,完全不被允许存在。」
「所以……你是因为这样才转过来的吗?」我忍不住问。
她睁开眼,那双红肿的眼睛透着一种看穿一切的神情。
我安静下来,点了点头。那一刻,我脑中浮现的是她手臂上那些交错的自残疤痕。
「我被霸凌。」她说得云淡风轻,彷彿在说别人的故事,丝毫没有遮掩的意思。
「真的假的?」我惊呼。
「你这个反应,是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被霸凌吗?」
「对啊,你这么有个性……」
「枪打出头鸟呀。」她耸耸肩,「那里的风气很保守,反正学校不喜欢我,我又反骨。既然格格不入,我就自己离开,没什么大不了的。」
「那……你手臂上那些疤,也是因为那时候吗?」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「你观察得很细緻耶。」她看着我,眼神里多了一丝玩味,「难不成你其实一直在暗恋我?」
「我观察你很久了。」我认真地回答。
「对啊。其实上学期我们一起修过一堂通识课,只是你可能对我没印象。那时候我就觉得你很酷,在护理系这种保守的环境里,我从没看过像你这样的女生。你很有自信,穿搭有个性,说话又落落大方,感觉跟网路上那些假掰的网红完全不一样。」
「太有趣了,没想到我竟然还有粉丝。」伍伊琳笑出声,眼底的红肿似乎消退了一些。
「但在社群软体上,我其实真的很假掰呀。」她滑开手机,给我看她的IG,「你看,哪个正常女生会这样拍照?这些滤镜跟角度,都是计算过的。」
「对呀,我不假掰一点,怎么拿流量去接业配赚钱?」她狡猾地眨眨眼。
「不管啦,我就喜欢你现在这种落落大方的样子。」
「我其实没有你说的这么好。」她压低嗓子沉重说着,「很多时候我其实都在偽装自己,至少比较不会受伤。」
「其实同学们都蛮友善的,你应该打开你的心房,然后会发现世界其实很美好。」我回应。
「你很正向耶,一直都这样吗?」
「我吗?我只是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糟糕,或许都还有转圜的空间,也许试着去接纳别人的好意也不错?」
或许是伍伊琳曾经受过伤,在看待事情上也会较防备,但我也希望她能重新敞开心房,不要在偽装自己,大方做自己,我相信世界上的好人还是佔为多数。
伍伊琳点点头,给我一个意义不明的微笑。但我觉得她是其实一个遍体麟伤的女孩,而不是我初次认识的酷女孩。
和伍伊琳深聊后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她了。她活得很真实,敢于摊开自己的伤口,也不怕别人把她过去的事情当成话题。在脆弱跟勇敢中,选择成为一朵带着刺却绽放得极其灿烂的野花。
实习第一週,我跟着学姊跑流程,才知道临床不是考试上的选择题,而是永远做不完的待办清单。
发药、换管路、量血压、追数值、交班,每一项都不能错,但每一项都在催我快一点。
我开始变得神经紧绷,连下班后走回宿舍,耳边都像还在响着护理站的电话声。更可怕的是,我知道这只是初体验。往后还有其他六大科要轮,现在的疲惫,只是预告。
君怡的实习比我早结束。她说熬过这两週,最难的不是技术,而是「人」。
病人有情绪、学姊有情绪、医师也有情绪,大家都在赶时间,没有人真的有空好好说话。一个不小心,就会扫到颱风尾。
她回诊所后听说有工读生要离职,便问我愿不愿意去面试。我犹豫了一下,最后还是答应了。毕竟饮料店再熟练,也换不来任何未来。
我打算实习后去面试,希望我的选择会是对的,一切都能顺利。
熬过实习第一週,我像是在跟时间赛跑,週六深夜就把报告飞快赶完。不为别的,只为了明天能理直气壮地,奔向有林家同的地方。
他说他已经回台南了,我先假装随口问他。
「你明天有安排事情吗?」
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。」
「中午我妈都会煮,感觉有点难,如果有空跟你说。」
我被思念蒙蔽了眼,心里想着:林家同,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
隔天,我跨上机车,耳机里导航指引着我一路向北。从高楼林立的市区到错综复杂的圆环,最后接上漫长的省道。铁道支线在右侧延伸,我骑过被烈日晒得发烫的农田,转入窄小的巷弄,在充满鱼腥味与叫卖声的菜市场里穿梭。
直到我看见那座妈祖庙。庙前的一隻黑狗对着我这陌生人狂吠,那声音尖锐得像是在警告,我吓得不敢停在庙旁,我随意找了个停车位,脱下安全帽。
我狼狈地停好车,摘下安全帽,汗水顺着鬓角流下。就在巷尾,我看见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背影。那宽厚的肩膀、站立的姿势,我甚至不用看脸,光凭影子就能认出他。
我正要喊他,一个女孩却从墙后的阴影处轻巧地走出来。他自然地牵起她的手,转身走进另一条小巷。
我像个幽灵般跟在后面。我想确认那是错觉,想确认那只是个长得像的陌生人。然而,当他们在小吃摊坐下,他绅士地为她拉开椅子,那专注的眼神对上她的脸时,我全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冻结。
我躲在电线桿的阴影后,颤抖着手传了讯息:「你吃饭了吗?」
视线死角里,我看见他的手机就放在桌上,但他始终没有拿起它。
那一刻,我想衝过去把热汤泼在他脸上,想歇斯底里地要个答案。林家同,你身边一直都有人吗?这就是你忽冷忽热的原因吗?社团照片里那个模糊的影子,原来一直真实存在于你的日常里。
我以为我会崩溃,但出奇地,我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灼热的愤怒与不甘。
我是谁?我到底算什么?我看着他们并肩坐着的背影,心底有个声音冷冷地响起:我不能输。
骑回市区的路上,我的脑袋没有空过一秒,我和家同在一起的所有画面,一幕一幕自动浮现,那些曾经甜到心坎里的举动,此刻全都变得刺眼又可笑。
原来那不是专属于我的温柔吗?
那些话、那些动作,是不是他早就练习得很熟了?
如果你早就打算这样,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放过我?
「为什么要招惹我?」我对着安全帽内的虚空发问,声音被引擎声瞬间搅碎。
我一路假装没事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到医院宿舍。
门关上的那一刻,我连鞋子都忘了脱,整个人直接向后倒在床上。
天花板在视线里晃了一下,我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
伍伊琳走过来,看了我一眼。
「你气色不太好。」她说。
「连你都看得出来啊。」我扯动嘴角,却发现自己连笑的肌肉都僵硬了。
「你不是去找你男友?怎么了,你们吵架了吗?」
我盯着天花板,心底那股不甘心再次涌上,但出口的却是另一套剧本:「没有,那个地址是错的。我没看到他。」
这是我最后的自尊。我寧可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找错路的傻子,也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劈腿的受害者。
「骑那么远还扑空,难怪你看起来这么累。」
她没有多问,只是拍了拍我的肩。
「我想静一静。」我说。
她点点头,没有追问,转身离开。
我这才慢慢坐起来,把鞋子踢掉,鑽进棉被里。
把整个人蜷缩起来,像是在保护什么。
直到那一刻,我才终于敢哭。
不是嚎啕大哭,只是眼泪自己流下来,
安静地,一滴一滴,渗进枕头里。
看着这行字,我突然觉得荒谬到了极点。我亲眼看着他为那个女孩拉开椅子、递上餐具,看着他用那双曾深情凝望我的眼睛对着另一个人微笑。而现在,他隔着萤幕,语气平淡地对我撒着最拙劣的谎。
「林家同,你真的爱我吗?」我在心底疯狂地吶喊。
回忆像是一把双面刃。我想起他抱着我时的力度,想起他曾低声说过只爱我的温热气息。如果那是真的,那今天那个女孩是谁?如果那是假的,那过去这些日子,我又是谁?
我的脑袋像是一台坏掉的投影机,反覆倒带那些情爱小事。我开始为他找藉口,或者说,为自己的卑微找出口:「也许那是他推不掉的前任?」
「也许他们快分手了?」
「也许……他正打算跟我坦白?」
我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「低调恋爱」。原来那不是保护,而是藏匿。我就像是被他豢养在阴影里的廉价分身,见不得光,却又自以为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。
最可悲的是,明明我是受害者,我却在担心自己才是那个「第三者」。
我想像着那个女孩。她知道我的存在吗?她也曾听过同样的甜言蜜语吗?一个阴暗的念头在我心底扎根:如果他们分手了,我是不是就能名正言顺地转正?只要他最后选的是我,这段羞辱是不是就能被洗白?
我不想要理性,不想要体面,我只想要林家同。
那种强烈的不甘心像毒素一样蔓延全身。我不准他去爱别人。我要他看着我,我要他像当初招惹我那样,最后只能选择我。哪怕这份爱已经开始变质,我也不想放手。
实习结束后,台中生活的一切像是按下了重置键。我辞掉了饮料店,穿上粉色制服,成了知名妇產科诊所的柜檯人员。我和君怡轮流搭班,学着掛号、消毒器材、擦拭那些冰冷的诊察椅。
在这个每天都有无数女人带着秘密、痛苦或喜悦进出的地方,我成了一颗沉默的小螺丝钉。然而,诊所里的漂白水味再浓,也掩盖不了我内心那股逐渐腐烂的佔有欲。
我没有拆穿林家同。相反地,我像是一个在暗处佈局的猎人,用尽心力想要得到他整个人。
「谁是正宫、谁是第三者」这类道德问题,在我的世界里已经失去了意义。我只要最后他选择的人是我。我想证明,我比那个「她」更值得被留下。
在台中的日子里,林家同依旧是那个完美的情人。他会在我疲惫时递上热可可,用那种温柔得近乎残忍的口吻鼓励我。但他越是完美,我就越是在他的瞳孔里寻找那个女孩的残影。
那个留着黑长发、笑起来眼睛像弯月般的女孩。她是那么优雅、那么无辜。
我总是想着:「如果你知道他现在用牵着你的手,正抱着我,你会怎么样?」
这种扭曲的优越感支撑着我。即便他在週末会消失两天,但在剩下的五天里,他就像是我的私人物品。
夜深的时候,房间只剩下一盏昏黄的灯,我没有说话,只是靠近他,用身体贴近他,像是在确认某种主权。
我闭上眼,让感官变得敏锐。
那种感觉像是草丛里的白兔,明知道危险,却还是选择走向野兽,既是献祭,也是交易。
我把自己当成筹码,押在这个夜里,试图用最原始的方式,把他留在我身边。
在黑暗中,我留下了痕跡,不张扬,却足够明显,像一个无声的记号,安静地烙在他的身上。
我没有说出口,但心里很清楚,我希望她看见。希望她明白,有些界线,已经被越过了。
也希望,她能因此选择退让。
我相信那个吻痕,他一定发现了。我不知道他回台南后,如何对那个女孩解释这道曖昧的红印;我只知道,他这次回台中后,对我的反应像被冻过一样,甚至换了一床全新的粉蓝色云朵床单。
那床单温柔、轻盈,却与林家同那种乾净俐落的气质一点都不搭。
我当然知道是谁买的。那不是一组床单,那是另一个女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隔空宣示的主权。但我依然选择装傻,这是我唯一的筹码,我怕一旦戳破这层薄纱,我就会连待在他身边的资格都失去。
这段不健康的关係像是一场缓慢的自我消磨,而家同也察觉到了。他开始躲避我的触碰,甚至在我还没提起「云朵」之前,就对我避而远之。
「你最近压力很大吗?」那天,他突然问。
「没有啊。」我摇摇头,笑得勉强。
「但我感觉你变了,」他盯着我,眼神里有一种防备,「感觉你……变得强势了点。」
强势?这两个字像一记耳光。不知情的人听了,或许以为我在这段关係里佔了上风。我突然想起伍伊琳说过,偽装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,而我现在正戴着最沉重的面具。
「可能实习和工作,真的让我长大了吧。」我维持着笑容。
我明明才是那个遍体鳞伤的人,但在林家同眼里,我那种近乎疯狂的执着,却成了让他窒息的强势。我将对那个女孩所有的嫉妒与恶意,全都导向了工作压力的藉口。
我没告诉他,我已经在深夜里无数次翻看过那个「云朵」的IG与Facebook。 我知道云朵代表的是谁,我知道她叫刘湘妘。
七年。刘湘妘与林家同交往了七年。那是一段我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跨越的光阴。难道我的出现,仅仅是林家同的一场「七年之痒」?
我不甘心。我不愿自己只是他生命里一段意乱情迷的插曲,更不愿只是那个用来止痒的工具。
Tom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递过一张纸巾。
我没料想到,时隔多年,当我再次亲口陈述那段内心的交战时,情绪依然会如此决堤。我握着那张轻薄的纸巾,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当年的不甘心。
「我那时候只能不断骗自己……」我哽咽着,声音在咖啡厅的音乐声中显得细碎,「我告诉自己他是爱我的,只要我不放手,我就还没有输。」
Tom沉默了片刻,开口时语气平静,却字字见血:「说句不好听的,你那时候透支自己的尊严。你以为付出一切很勇敢,但在他眼里,那样的你,根本不需要被珍惜。」
他的话过于直白,像是吞了「诚实豆沙包」后吐出的利刃,精准地刺入我最想掩埋的伤口,我感到一阵微微的抽痛。
「可是,那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。」我低着头,看着纸巾被泪水浸透,「我明白,如果我不那样留住他,我会立刻失去他。」
「那……」Tom看着我,眼神里多了一丝探询,「湘妘后来知道你的存在了吗?」
我深吸了一口气,视线看向落地窗外,脑海里浮现出诊所里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
「我想,她后来是知道了……」我的声音低了下去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