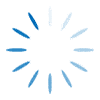看,这就是美的最高境界
第二天,下午两点左右,我又确认一遍宋钦文发来的定位,换好衣服,打车来到训练基地的门口。
“抱歉,等很久了吗?”宋钦文擦了把脸上的水,光溜溜的背上粘着一条毛巾,一副浑身溼透的样子。就在这时,阳光从训练基地的大门鑽进来,刚好照在他头发上,亮晶晶的,顏色漂亮得像是某种黑色鑽石。
我看到几滴水顺着他的头发淌下来,画笔一样描绘过他的侧脸,一路滑到他的下巴,最终掉了下去,落在地上。我动了动喉咙,眼神开始飘忽,不知道该看哪里:“你刚从水里出来?”
宋钦文抓住我的胳膊,一把把我拽进建筑里,随后收回撑门的手,点点头说:“今天睡过头了,刚刚游完白天的七千米,天黑之后还有七千米。”
出于心虚,我放低了声音,连问话都变得小心翼翼:“我能随便进来吗?万一被你的教练或者队友看到不太好吧……”
宋钦文盯着我看了会儿,忽然笑起来:“别担心,现在基地里没有其他人,整个教练组都带队去延京参加冠军赛了。他们说我身上揹负着‘亚洲的荣耀’,所以更希望我留在寿丰,全力备战两年后的马德里奥运会。”
我舒了口气,放下心来。看到我的样子,宋钦文什么都没说,只是朝楼梯的方向偏了偏头。他一迈开脚步,我就立马跟了上去,忍不住在他身后发问:“你平时每天都要训练?教练不在也不休息一下吗?”
宋钦文走上楼梯,回头朝我一笑:“游泳是一项必须保持练习的运动,一旦松懈下来就很容易退步。昨天我也是游完七千米后才心血来潮,决定去人民公园转一转的。”
所以我们俩的相遇根本就是个意外?我回想起前一天宋钦文的种种表现,越发感觉他这人迷雾重重,捉摸不透。可能是我的眼神透露了什么讯息,宋钦文抓着楼梯扶手看我,一下笑出声音:“你知道,运动员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自己制定一套计划,再督促自己严格执行计划。对我来说,去人民公园和遇到你都是计划外的事情。”
我嘟囔了句:“对我来说也是个意外。”
这是真话,我甚至不知道我这辈子还会不会遇到更离奇的意外。
来到三楼,宋钦文带我穿过走廊,走到泳池边上,停下了。一眨眼的工夫,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条泳裤,递到我面前,问我:“要不要和我游一会儿?”
游泳?我已经很多年没游过泳了,都不知道自己记不记得那些基本功。揣着这个念头,我站在那条写着“奋力拼搏,超越自我,挥洒激情,豪取佳绩”的标语下,一时进退两难。
犹豫一阵后,我抓住泳裤的边缘,随口问了句:“这是你的私人物品?”
宋钦文轻笑了声:“当然不是我的,队里有很多备品。你放心,这条是新的,没有人穿过。”
水汽在我们之间蒸腾。我看向宋钦文的眼睛,深感在这种眼神的注视下没人会忍心说出拒绝的字眼,就连开口发出声音都变得很难。
过了十多分鐘,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,整个人已经换好泳裤,和宋钦文一起进了泳池。我眨眨眼睛,看到他手臂一抬,没划几下就游到了泳池的另一边。紧接着,他做了个到边转身的动作,一瞬间又回到我身边。
宋钦文先是扎进水里,很快又像棵破土的树一样长出水面。他仰起头,甩掉脸上的水珠,这一刻的角度和线条全都刚刚好,只可惜我们戏剧社的社长不在这里,不然他就能用他那双特别善于发现美的眼睛鑑赏一下宋钦文,然后评论一句“看,这就是美的最高境界”。不过我的眼神也不比我们社长差,我承认宋钦文出水的样子就是很美,任何有眼睛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一点。他就像一座在希腊神庙里沉睡过久的雕塑,受到水的滋养才终于悠悠转醒。
不得不说,宋钦文完全不像不久前才游完七千米的人,仍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。我抹掉鼻尖的水珠,把鬓角的头发别在耳朵后面,好奇问他:“你不累吗?”
“七千米不是什么问题,教练组的要求是日均一万两千米,所有人都习惯了。我想多训练一些,就给自己又加了两千米。”一滴水珠掛在宋钦文的嘴角,像在点缀他的微笑,“而且我们都很清楚要怎么分配自己的体能,平时训练不会太累。”
我不懂游泳。一旦涉及到什么起跳,打腿,控制核心之类的技术问题,我通通一问三不知,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过,作为这项运动的门外汉,我仍能看出宋钦文的臂展很长,泳姿很好。
这么想着,我来回打量宋钦文的两隻肩膀,到底没忍住心里的疑问:“我能知道你有多高吗?”
“一米九三。”宋钦文抹了把头发,朝我笑起来,“我十几岁的时候在省队测过一次骨龄,当时的教练说我可以长到一米九六,我太相信他的话了。别看三釐米不多,但是就差这三釐米,我没能成为队里最高的队员。我们这批运动员里个子最高的是彭哥,他有一米九五。”
说完,他话锋一转,把话题引到了我身上:“其实你也很适合做游泳运动员,手长脚长的人划起水来时效很高。”
我摇了摇头:“我不行,身高不够,只有一米八五。”
宋钦文点了下头,表示理解,嘴上却说:“一米八五应该也够了吧?我们队里最年轻的小队员也只有一米八七。”
我继续摇头:“我年龄太大,游不了了。”
宋钦文摸了下鼻尖,又点点头:“你才二十一岁,还很年轻,但是算了就算了吧。一旦做了运动员,你的身上肯定到处都是伤。”
说到伤病这个话题,我顺势指指他的左肩:“你这里是不是做过手术?”
宋钦文没有回答我的问题,而是带着微笑反问:“你昨天回去看了很多关于我的新闻?”
既然他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,那我也不打算老老实实回答他。我抚摸着那隻肩上的疤痕,开始自说自话:“你在备战蒙特利尔世界盃的期间训练过度,导致肩袖重度撕裂,医生说必须要做肩关节镜修復手术。术后还没出恢復期,你就坐飞机去了蒙特利尔。那次比赛非常痛苦,你每游一下都像被浪花凌迟,最后全凭弔着一口气才拿到那块蝶泳单项的金牌。回国后,各大媒体一拥而上,哪怕挤破脑袋都要预约你的採访,还纷纷发表文章讚美你是‘水中雪雁’。”
宋钦文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,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:“你怎么这么可爱?只用一个晚上就补了这么多课。”
他对“可爱”这个词好像有什么误解。我说:“我是学文学的,记忆力很好是我的基本功。”
我不知道这句话哪里刺激到宋钦文了,他陡然潜入水下,一把抓住我的脚踝,稍一用力就把我拖下了水面。好在我反应很快,趁着入水之前憋了口气,被他折腾一时半会儿不成问题。计划得逞后,宋钦文抬高我的脚腕,使劲一拽,我重心不稳,整个人直接朝他的方向撞去。就这样,我的一条腿撞上宋钦文的胸口,只有脚踝以上的部分探出了水面。接下来,没有任何预兆,宋钦文突然凑近我的脚踝,用脸慢慢刮蹭起来,动作亲暱,笑容曖昧。我被他搞得心里一惊,在水下吐出好几口空气,差点呛水。随着一阵咕嘟声响起,气泡接二连三升上水面,宋钦文连忙放开我的脚踝,游到水下,嘴对嘴给我送了点空气,然后抱住我的腰,把我捞回水面。
我一边喘气,一边虚心接受宋钦文的点评:“你还没掌握游泳的基本功,所以没办法学习其他更难的技术。”
我摸摸额头,人有点无奈:“我都说了我不擅长游泳,天生就没有运动细胞……”
不知道是不是良心发现,宋钦文居然主动靠过来帮我整理头发。这会儿我们并排靠在水里,离得太近了,他的鼻息一直往我颈边喷:“你的头发有点长,溼了还挺好看的。”
我瞟他一眼:“有什么好看的?我平时头发没这么长,只是最近懒得去剪。”
这次换做宋钦文摇头了:“不管你的头发是长还是短,肯定都很好看。就像你穿着衣服的时候很显眼,现在这样不穿衣服反而更引人注意。”
我一下弄明白了。这种剧情不就是一款经典的见色起意吗?难道他们体育生真的都像口口相传的那样,精力旺盛到无处宣洩,每天都迫不及待把没见几面的人骗到自己床上?
我沉默下来,想得眉头直皱。宋钦文打量着我,用声音唤回我的注意力:“郑慈,我没有别的意思……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”
太不可思议了,他竟然能看穿我在想什么。
我立刻展开手臂,往前游了两下,转身和宋钦文面对着面:“没有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我说的都是实话,不信你可以去问孔教练或者科斯蒂亚教练。他们在国家队执教了五年,队里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出现过作风问题,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……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轻浮,那么随便,我是认真的。”宋钦文抓抓耳朵,目光落向水面,声音也低了下去,“在遇到你之前,我一直不明白什么叫一见钟情。”
我还能做什么反应呢?他看上去和电视採访里的那个宋钦文一点都不一样。那个宋钦文好像比我眼前这个宋钦文更成熟,更自信。就算和主持人谈起“失败”这种梦魘般的话题,他也不会回避镜头,反而能轻松一笑,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两句话。一句是:“没有人不害怕失败,但是每天提心吊胆没有用,最重要的是起跳的那个瞬间。在我心里,无论技术好坏,成绩如何,每一个完成起跳的人都不算失败者。”
另一句是:“站上领奖台的秘诀?应该没有这种秘诀吧。我自己的话,儘量不在赛前想象输掉比赛这件事。科斯蒂亚教练告诉过我们,看到泳池的时候,你不要把它当成比赛场地,你要想:此处通往繁星。”
隔着几十公分的距离,我看着这个从电视屏幕里走出来的人。他的嘴巴抿成一线,眼神在水面上漂来漂去,彷彿迟迟无法拋出的锚,这副焦躁不安又缺乏自信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在说谎。
泳池里的水包裹着我的身体,不知道为什么,我忽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。
我想我可以相信宋钦文。
不过有一件事还需要确认。我说:“我学过统计学,我知道‘一见钟情’的概率有多小……你真的是昨天在人民公园对我一见钟情的?”
宋钦文一怔,继而笑出来:“你就这么想知道答案吗?以后我会告诉你的,前提是你要和我在一起。”
好吧,好吧。随便吧,管它呢?世界上有八十亿人,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的概率是八十亿分之一,宋钦文已经是我的八十亿分之一了,我真的还要计较什么概率问题吗?
比起游泳,我更不擅长的是数学。我早就应该放弃它了。
我又往前游了一点,先前那几十公分的距离随之消失了。我停在宋钦文面前,双手捧住他的脸,咬上他的嘴唇。
回应我的是波动的水面和一个来势汹汹的吻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